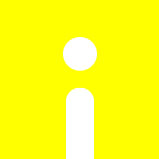用成績來決定體罰,我覺得這是最不負責任的方法!從頭到尾,眼鏡仔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彎腰駝背,近乎無聲地呼吸著。他的四肢不長,又佝僂著身軀,整個人看起來變得更小隻了。他直盯著自家木桌上的紋理,始終沒有抬起頭來看我們一眼..
文:吳曉樂
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我很少想起眼鏡仔。他是我第三個家教學生,家住台北榮星花園附近。
說到眼鏡仔,整個人乾乾瘦瘦,捏不出幾兩肉,倒是戴了一副很笨重的眼鏡。眼鏡仔說,他近視已經七、八百度了,醫生曾恐嚇他,再不控制一下,眼鏡仔長大後可能就要失明了。可是,眼鏡仔控制不了,他每天都被成績綁架了,每天都用眼過度。
隨著年紀漸長,或許是對於往事的一種懷戀,我變得很常想起我最初的幾個學生。
除了眼鏡仔,對,就除了他。
這麼多年過去,在回憶的長廊上,一一唱名我教過的學生時,我總忽略眼鏡仔。想起他總是不愉快,甚至連「榮星花園」四個字,在記憶上也成了一種負擔。
令我不愉快的,並非眼鏡仔這孩子,相反的我很喜歡他,但想起眼鏡仔,就無可避免地,必須同時面對在眼鏡仔背後,那些我無力去處理的人事。
眼鏡仔的媽媽,不妨稱小圓媽好了。她給人的印象就是圓滾滾的,臉圓手圓,身材也圓。第一次見面,我就見識到小圓媽強勢的作風。她語速很快,連珠砲地朝我射來,說話時手腕的擺動幅度也非常大:「老師,我跟妳說,我這孩子就是笨,做什麼事情就是慢,怎麼教都教不會,之前的老師都放棄了。」小圓媽抬眼,扳指一算:「妳是他第十個、還第十一個家教老師。我跟他說,這次再沒效,我就一個老師也不給他請了,放他自生自滅!」
我尚未接腔,她又急著開口:「老師,我兒子如果不乖,或者題目寫錯,妳就用力給他打下去,孩子有錯,就是要教育,我不是那種小孩子被打就反應過度的父母。」
聞言,我知道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但是,阿姨,我不打學生的。」
小圓媽的動作慢了下來,她從上到下,仔細掃視我一次:「我看妳的資料,妳才大學一年級,十八、十九歲對吧? 妳們這一代的年輕人,聽到體罰就皺眉,好像體罰是多殘忍的一件事!」小圓媽哼了一聲,嘴角扯出一抹冷笑:「會這樣想,是因為你們欠缺教小孩的經驗,以為輕聲細語,愛的鼓勵,小孩子就能乖乖向學,順利進步了。事情絕對沒有你們所想的這麼簡單,我提醒在先,妳教過我兒子之後,我們再來討論打不打小孩的問題。」
在小圓媽唇片翻動、口沫橫飛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詭異的景象——
從頭到尾,眼鏡仔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彎腰駝背,近乎無聲地呼吸著。他的四肢不長,又佝僂著身軀,整個人看起來變得更小隻了。他直盯著自家木桌上的紋理,始終沒有抬起頭來看我們一眼。
他的反應,彷彿這場對話與他無關,他是局外人。
結束與小圓媽的初步接觸,我跟眼鏡仔來到他的房間。
在我們打開試題本五分鐘之後,眼鏡仔走入我的內心最柔軟的角落:我指出一個錯誤,那只是個非常細小、無關緊要的小瑕疵,眼鏡仔的反應卻非常劇烈,他的肩膀很快地拱起來,背部連動地微彎成弓形,他的臉側向與我背反的方向。
整個動作一氣呵成,近乎反射。
我緊張地問:「怎麼了嗎?」
「我以為妳會打我。」
「我為什麼要打你?」眼鏡仔的問題令我震懾不已。
「媽媽不是允許妳了嗎?」
「但我不也告訴過你媽媽,我不會打你嗎?」
眼鏡仔不置可否地抿了抿嘴,低頭,右手捏著試題本,指甲陷了進去。
「媽媽跟之前每一個家教建議,只要我犯錯,就打下去;我再犯錯,就再打下去。打多次一點,我就會記得不要再犯相同的錯了。」好像在說給自己聽似的,眼鏡仔的聲音越來越小:「不過⋯⋯我好像真的很笨,我被打這麼多次,還是很常犯一樣的錯。上一個家教是男的,打人很用力,我很怕他。他最後還是辭職了,他跟我媽抱怨:『我打妳兒子打得都累了』。」
眼鏡仔似乎想到什麼,抖了一下,又說了下去:「那個家教走了之後,媽媽對我發飆了很久,她說我很笨、很沒用,沒人願意教我,害她必須一直找老師。」
眼鏡仔沒再說話,他把手放在膝蓋上,上半身小小的。
「我不會打你。不管你錯再多題。」
「真的嗎?」眼鏡仔很淡漠,不怎麼相信的樣子。「之前有個女家教,好像跟妳一樣大,還是比妳大一點點,她也是跟我說:『我不會打你』,但是到了最後⋯⋯她還是氣到忍不住了。她說:『你真的很笨,我沒遇過像你這麼不受教的學生』。老師,我跟妳說,我媽是對的,我真的很笨,又遲緩。有一天,妳也會受不了,想要打我的。」
他的頭仍舊低垂著,我聽見他的呼吸有些亂了。
我遲疑了一會,決定重申立場:「我是真的、真的不會打你。」
「為什麼?」
「我也是接受體罰長大的學生。」
聽到這句話,眼鏡仔微微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視線又急忙轉向桌上的橡皮擦。
「我國中念前段班,理化老師是個一天到晚嚷嚷著要退休的老頭,他基本上沒在教書了,只立下一個規矩,八十分,少一分就打一下。我有個單元真的搞不懂,考了六十一分,被打得死去活來。之後,我狂寫、狂算題目,基測時我理化一題也沒錯。」
「妳好強。」
「不,一點也不。上了高中之後,我的理化很爛。我很困惑,想了一段時間才明白,在過去,我讀書是怕被老頭打,自己本身其實沒有讀理化的樂趣,等到升上高中,沒人打我了,我反而不曉得怎麼讀書。又因為老頭的關係,我很討厭理化這一科,一點也不想碰。」
看眼鏡仔似懂非懂的模樣,我補充道:「用成績來決定體罰,我覺得這是最不負責任的方法,當下或許呈現出不錯的成果,但之後也可能會製造出更多問題。」
眼鏡仔默默地聽著,沒有應聲。
「所以,假設你考差了,我們就換個方法,你如果再考差了,我們就再換個方法。我不想打學生,打學生也代表我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跟耐心。我想解決問題。」
「真的嗎?」眼鏡仔看著我,我們的眼神有了交會。
我終於看清楚。藏在厚厚的鏡片後頭,眼鏡仔的眼睛其實又圓又亮。
*
在沒有體罰的前提下,我得正視一個事實:眼鏡仔教起來確實令人有些情緒。
一模一樣的題型,也許上個分秒才耐心敘說,眼鏡仔仍無法正確作答。更多時候,我已經極盡暗示之能事,只差沒直接伸手指出答案了,眼鏡仔的思路,卻像是有誰猝然設了個路障,沒辦法再前進了。我看得更久一點,發現眼鏡仔對於「寫下答案」這動作特別有心魔。
每一次,握著筆,要寫下答案了,他的眼睛開始骨碌碌地轉,在空調恆溫二十五度的室內,他的汗水大肆奔流。見他這麼難過,我也跟著屏息,空氣稀薄了起來,不由得抬手搧了搧。
也有幾次,眼鏡仔的筆尖抵在紙面上,緊張不安的眼神頻頻對我送來。那眼神,像是在默讀我心底的念頭,也像是在預防我下一秒鐘的動作。
幾次心理的攻防,我忍不住開口了,請眼鏡仔放過自己,也放過我。我告訴他:「你不用緊張,你寫錯了,大不了我重新說一次,我不會打你。」
眼睛仔吞了吞口水:「之前的老師,都會盯著我看,一題一題跟,只要我寫錯了,他就馬上巴我頭,好幾次,我的眼鏡都被拍掉在桌子上。」
「是你先前提過,那個『打你打得都累了』的老師嗎?」我在腦海搜尋可疑人物。
「嗯。」眼鏡仔維持一貫的淡然,點了點頭:「他是媽媽請的家教裡面最貴的,補習班名師。他跟媽媽保證,沒有他救不起來的學生,媽媽於是給他很高的時薪。一小時,好像是一千二百塊吧,還常常加課,一個禮拜,可以上到六小時。可是,我的成績還是時好時壞,媽媽有時候受不了,會怪老師,老師跟著急起來,就一題一題盯我,如果我寫錯,他會馬上巴我頭,或者拿熱熔棒打我的手心。」
「每一題?」
「對,那個老師坐得很近,這麼近啊——」眼鏡仔用手比畫出距離:「他的視線會黏在我的考卷,等我作答,只要我寫錯,完了、死定了。有一次,段考前一天,他拿一張他自己出的題目給我寫,我錯超過一半以上,他非常、非常生氣,卯起來打,拚命用熱熔棒打我小腿,我很痛,可是我不敢哭。」
「你媽媽知道,那個老師,打你打得這麼兇嗎?」
眼鏡仔搖搖頭。
「為什麼不告訴你媽? 那個老師叫你不能說嗎?」
「不是。」
「那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眼鏡仔有點不自在:「老師打我,是我的錯,我沒有把題目寫好。我跟媽媽說,媽媽只會更生氣,搞不好也會打我一頓。」
我不禁懷疑:眼鏡仔不是笨,也不是遲緩。
眼鏡仔不過是個嚇壞的孩子。
平常,講題目的時間,順著題意一步一步進行拆解、推導,這過程眼鏡仔可以跟得很穩很好,此時進行口頭提問,他也能答得很理想。然而,一旦面臨把答案用鉛筆謄上去的瞬間,眼鏡仔就像是中了石化術,從頭到腳僵硬了起來。
過往的經驗告訴他,一旦犯錯,拳腳就伸了過來。所以,他在答題上,眼前彷彿有個看不見的關卡,他無法跨越這關卡。反覆質疑,踟躕再三。一場四十五分鐘的考試,他可能浪費了三十分鐘,只為了跨過一道「我可能會寫錯」的關卡。
真要給眼鏡仔下一個結論,我會說,這孩子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信心。
他不相信,犯錯是件很尋常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因為,過去幾任老師不給眼鏡仔犯錯的空間。
眼鏡仔一點也不遲緩,他只是被套上了重重枷鎖,是以他走得較常人忐忑,較常人戒慎,最終不免給人一種笨拙、遲鈍的印象。但他並沒有外界所料想的蠢笨。
模擬考成績下來那天,台北細雨斜織,我站在門外,還來不及束好雨傘,就聽到一陣急遽的腳步聲,從遠至近,小圓媽三步併作兩步下樓,門一打開,她臉色有些古怪。我一進房,她便如影隨形地跟在後頭,一開口就是抱怨:「哎,老師,我跟妳說,這孩子真是沒救了。我真想不透,我給他的讀書環境這麼好,為什麼這孩子就是沒辦法爭氣點?」
「考得很不理想嗎?」
小圓媽說:「我跟他父親給他估計理想的P R值是九十三,他只考了八十三,P R值只有八十三。老師,妳告訴我,在台北市,這樣的成績,哪一間明星高中要他?」
眼鏡仔的P R值為八十三,一個簡單的理解是,眼鏡仔的分數高於該次測驗全國約八十三%的學生。照理說,該是很亮眼的成績。但是,台北市的競爭確實很激烈,一個細微的差錯,就是下看一到兩間學校。
「老師妳看,我都給他請名校的家教了,他還給我考這樣。」小圓媽的話中多少有怪罪我的意思。我習以為常了,這份職業,領的是他人眼紅的鐘點,雇主們自然有一套「教學品質檢測」的標準,最典型的,莫過於定期舉行的段考、模擬考。若學生考不出亮眼的成績,家長最直白的心態莫過於:「那我砸大錢請你來做什麼?」
一步一步爬上樓梯。客廳裡,眼鏡仔站著。更精準的說法是,罰站著。
走進客廳,小圓媽不忘先給我倒杯茶水,同時也給自己的茶杯注入新茶。稍事休息之後,她把眼鏡仔的成績單取來,開始一科接著一科質問。
「數學為什麼錯了六題? 上次你才錯三題。」
「你不是告訴我,這次社會比較簡單? 卻錯了快要十題?你真的有讀社會嗎?」
「還有英文,從幼稚園就給你補英文,沒辦法拚一次滿分?」
眼鏡仔支支吾吾,脹紅了臉,不知從何辯解起。
小圓媽越說越激動,一個箭步上前,掃了眼鏡仔兩個耳光,清脆的巴掌聲回響在客廳之中,伴隨著高八度的謾罵:「你怎麼可以這麼不成材啊!你爸的同事都在問你準備得怎麼樣,我哪好意思說,我的兒子在台北市可能找不到好學校念。」
兩個巴掌,我跟眼鏡仔都嚇壞了。
眼鏡仔抬起頭來,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眼神中有驚訝與屈辱。但他很快就回復到他習慣的處理方式:垂下眼,拳頭緊握,把視線交給地面,一動也不動。
小圓媽的嘶吼一波接著一波,她將許多陳年往事一一掏出來,內容儼然是眼鏡仔截至十四歲的失敗史,包括幼稚園老師對眼鏡仔不怎麼樣的評價、失常的國小入學考以及不上不下的國小畢業成績⋯⋯等等。完全不顧我這個外人在場,小圓媽徑自開展清算式的數落,她忘了叫我坐下,也可能是故意的,總之我形同被罰站,跟眼鏡仔一起站著聽,感覺像是聽了一輩子,結束時,偷瞄一眼時鐘,才不過半小時。
小圓媽睏倦地坐回沙發上,朝我們揮了揮手,說:「老師,妳可以上課了。」
我不想上課,倒是非常想逃,腦中閃過一百個逃離現場的藉口,但我又一一刪除那些選項。我心明眼亮,假若我此時開溜,眼鏡仔的處境將變得更為艱難。
一同經歷暴風雨的洗禮,我與眼鏡仔之間,不免萌發出一種近似革命情感的牽絆。我非常、非常想離開,但我不能離開。
我走了就是背叛。
我幾乎是硬著頭皮,踏進眼鏡仔的房間。眼鏡仔拖著腳步,跟在我的身後。
桌上,課本攤開了一半。
我們分別坐了下來,彼此神容尷尬,動作生硬,彷彿這是我們第一次上課。
淚水在眼鏡仔的眼眶打轉,沒有掉下來。他撐得很勉強。不在我的面前掉淚,似乎是他所僅存、用以維護自己尊嚴的手段了。
為了填補我們之間的空白,我開始動起嘴巴。不過,我的聲音有氣無力,在同一頁轉了十來分鐘有餘,好像鬼打牆,怎麼樣也走不出去。眼鏡仔很細心,察覺到我的失落,他突然轉過身,面向我,「對不起,老師,我讓妳失望了,我真是太笨了。」
眼鏡背後的雙眼,脹得紅通通的。
我看著眼鏡仔,心中百感交集。我相信眼鏡仔很困惑。他無法釐清自己挨揍的原因,成績真的能證明些什麼嗎?若有,到底是證明了什麼?
我也陷入了困惑,我個人想問的是,在我們執意相信成績證明出來的結果時,我們是否並不在意,這孩子本質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成績無法證明的。
我沒有這能力,去協助眼鏡仔澄清他的困惑,我也希望有誰來澄清我的困惑。
我只能避重就輕地告訴眼鏡仔:「你不笨,P R八十三,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拍拍眼鏡仔的肩膀,沮喪地再也吐不出話來。
那堂課,結束得很苦澀。我們氣色委頓,像是一起打了敗仗的士兵。
(編取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電視劇書衣版):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一書 /網路與書出版 /博客來 授權刊載)
相關文章:
我有話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