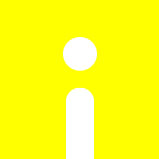「常青藤計劃2017·青年策展人項目」
入選展覽之一
「何處不圍城」
策展人:張予津
策展人說
人只要活著,四處皆城。「圍城」是一種生命隱喻,它作為公共情感狀態永恆貫穿於人生歷程的始終,無論你處於何種身份與立場,基於怎樣的生活經驗與視角,都會面臨被動與主動選擇間的彷徨遊離,以及理想與現實間的矛盾交織,這也是活在當下的我們一代人的困惑與面相。
思想匱乏、價值失衡、充滿誘惑的今天,我們正在持續遭遇殘酷的生存競爭、生活壓力與精神危機。「如何擺脫困惑」是大家無法規避的時代問題。該展覽,策展人將對「圍城」概念進行分層解構,組織13位藝術家展開文學閱讀與摘抄、文體自由的手記寫作以及基於各自文本內容與策展人形成的即時對話,以實現對藝術創作與日常閱讀經驗間互為關係的挖掘與探討,作品與創作觀念的再造與重思。同時,藉由兩種語言(圖像+文本)並置構建的「閱讀」場域,也將串聯起展覽主題的內在邏輯,為精神困境的治癒與解惑創造可能,為重燃觀者閱讀熱望與當代藝術審美欲營造視覺空間。在這場實踐中,手記不再只是作品的註腳,而是藝術家根植於藝術、閱讀、生活、文化等命題的私人絮語,包裹著性格、情感的溫度,共通的愛與怕、焦慮與迷惑。無論是文字還是作品,因其流露的真實而營造情感的親近,以慰心靈與信仰的缺口,亦是為驅散精神之圍城,走出理想主義與幻象破滅、目的消解的消極循環,正視此在與未知做出的積極努力。這是我與藝術家互助寫作的初衷,字裡行間里是我們一種關乎文化理想的默契。
策展手記(一)
一個青年策劃者的獨白:在現實與理想中博弈
2016年,在「常青藤計劃·青年策展人項目」首次推出之後,我寫了一篇類似於項目報告的評論文《成為青年策展人,你準備好了嗎》,並發表於學刊《北方美術》。作為這個項目的策劃執行者之一,我是在向自己發問,是對自己碩士畢業工作三年來個人現實處境的自我懷疑,也是在讀書時代職業理想與正在承受的殘酷現狀間不斷博弈之後的個人化感悟。老實講,當時的狀態並不好,甚至可以說是極度糟糕。當項目成功舉辦的成就感日益消退,巨大的焦慮反而空前來襲。每每想到入選項目的年輕策展人不過長我幾歲,卻成功為自己找到了未來前行的方向和目標,我為自己匹配不上夢想的才華與機會惶惶不可終日。
相信對於大多數與我一樣,專業美術院校史論或者藝術管理專業碩士畢業的同行,一定都苦於自己在展覽項目中僅擔任策展助理或執行的身份,期望在未來策劃一場自己擔綱策展人的展覽。而首先要強調的是,在我心目中,「策展人」始終是高門檻的位置,並不是隨意召集藝術家和作品攢一個展覽並在上面挂名的光鮮頭銜,這種展覽的組織者並不是我想要成為的「策展人」。
「策展人」是一個非常考驗個人綜合能力的工作,需要兼具深厚的學術素養、靈活縝密的思維邏輯、把控全局的組織管理能力、良好的寫作能力、與人溝通對話的人際交往能力等,同時還要時刻保持對社會、時代發展趨勢及個中現象問題在感知上的敏銳觀察力和吸納新事物的創造力,始終走在觀念和文化探索的前沿。策展人、批評家盛葳曾調侃「策展人像是服務性的第三產業」,一語道破該職業對從業者全方位素質的考量,也提出了更高的進入標準,即策展人是綜合體,既是策展學術觀念的提出者,展覽的策劃者,也是藝術實踐的創作者,展覽是他與藝術家合力完成的作品,是有機生產和能夠提出研究議題的成果。
知曉以上要求的我,反觀自身更是陷入對未來方向的迷茫,甚至是絕望。另一個令我格外無助的是成為真正策展人之前,策展執行工作的繁雜瑣碎,還有所得甚微的物質回報。一面是生存的窘迫,一面是職業現狀與理想的落差,當然還有內心的不甘心與身份歸屬感的缺失,導致我幾度在同代各領域結實的朋友中尋求情感的共鳴,我在交流中逐漸發現,我的狀態或許並不是個案,而是共性。
關於這種狀態的反思和警覺,在2017年春我閱讀了微信朋友圈瘋傳的《最近的北京讓我有點難過》等一系列「逃離北上廣」文章后,真正臻於頂峰。整夜整夜的失眠結果,是我開始想要藉助藝術的方式與藝術家和公眾共同直面處境,找到癥結,在詰問中治癒和救贖,也是為了實現自己內心鬱結的排解,在大家的情感交流中尋覓一絲溫暖和慰藉,收穫一種內心的回歸和平靜。
美院讀碩士時,許知遠在《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中對90年代大學生無色青春的控訴帶給我的觸動歷歷在目,而今我們這代年輕人的青春,之所以惶恐焦慮,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除了個人因素,是不是還有時代、社會大背景的裹挾?無論是對前途命運、人生方向還是價值觀、世界觀、身份的選擇,我們總是處在通往各種道路的十字路口,對每一條路都是既愛且恨,對錯失的和擁有的也總是患得患失。
也是巧合,在與讀書時藝術社會學導師郝青松的一次閑聊中,我把這種困惑和呼之欲出的表達慾望跟他說起,他告訴我:「其實每代人的青春都曾迷惘,徘徊是常態,在現實與理想間,在各種身份和地域的選擇間,這種矛盾狀態幾乎伴隨著每代人的青春期,甚至蔓延至人生每個階段。」由他的話,我展開了對人類群體情感狀態的隱喻性想象,想到了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外面的人想進來,裡面的人想出去」。
的確,方鴻漸的境遇不是特殊時代的個例,他跨越時代分野,成為眼下時代人群的縮影,毋寧說「圍城」之態是人類族群生命歷程里永恆存在的困境,人只要活著,四處皆城,這也是現代人群的癥候,是能夠誘發大家抒發慾望的主題。這便是我策劃「何處不圍城」展覽的靈感來源。
「圍城」里的青年
展覽的主題定下來的瞬間,我整個人是振奮的。兩天時間裡靠著腦子裡一股子熱乎勁兒趕出一套草案,迫不及待拿給郝青松老師看,並很榮幸邀請到他擔任展覽的學術支持。在方案里,我將創作人群圈定為青年藝術家,出於我自身屬於青年之列的考慮,同時也認為成長期擁有很多選擇和機會的青年群體,更易深陷圍城內外困頓不堪,且大多數缺乏與之對抗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人生何處不「圍城」,誰不是在現實和理想衝突交戰的「圍城」中兜轉,渴望一場酣暢淋漓的救贖?「如何擺脫困惑」是橫亘於同代人面前的共同渴望。對青年藝術群體而言,雖然不再拘泥於父輩對宏大歷史敘事的沉迷,卻將創作引入另一種始料未及的極端:在盲目追求「性格」特質的過程中倒反迷失了「自我」,個體的過度膨脹促成集體意識的缺失,伴隨碎片日常的卻是對身份認同及選擇的困窘。因此,新一代創作者需要將「自我」作為被時代裹挾中的「個體」進行多維度的獨立思考,以填補創作內容與內心世界的蒼白無力。
圍繞「圍城」之態,我開始考慮符合主題邏輯的藝術家。關於選擇標準,我希望選取的藝術家在慣常的創作中與時代、社會、文化不再表現為對抗和撕裂感,而是表現為一種自發走近、審視的文化自覺。同時,藝術語言也盡量避免呈現出絕對自我的傾向和流於視覺形式的空洞表達。帶著問題意識和人文情懷去關注當下的「自覺」以及把「自我」置於社會大環境浪潮之中去獨立思考的態度,在我看來才是青年藝術家們為免於創作個體走向價值虛無、自我迷失應該做出的革新。任何源於個體經驗的創作都無法擺脫因周遭環境變遷造成的潛移默化影響,換句話說,「圍城」所映射的焦躁不安與茫然無措究其誘因,是與多元並置的危機時代互為粘連的。群體的困惑同樣是青年藝術家所面對的創作語境,當藝術成為喚起公眾與藝術家間情感共鳴並隱含反思的審美實踐,才能葆有持續涌動的創造力和實驗性。它或許無法解決社會進程中的本質問題,卻可以提供一種更接近人性的文化態度與批判視角,亦為解惑與治癒創造了可能。
徐跋騁、張釗瀛、楊莉芊、劉豪格、胡佳藝、樊寒冬幾乎是我第一時間想到的邀請人選,也是在江夏然一件高聳的裝置作品中,「巴別塔」的概念一閃而過,我開始興奮,感覺可以在「圍城」主軸線之下細化為幾個單元版塊彼此相連卻又自成議題。「巴別塔」直插雲霄,繁華美麗,是舊時代人類有限能力的標誌,亦是奮不顧身去營造的幻象之城。而在我們的時代,夢開始的地方也總有對理想城邦的美好憧憬,如赤誠少年離開故土邁向遠方,為它屈服,充滿夢的想象。卻在不斷接近的過程中,目睹完美的塌陷,以及幻象之下的滿目瘡痍。人人自危的當下,無一人得以倖免 。而在藝術家的認知範疇,同樣可以突破個人處境的局限視角,轉而以他者之身份對宏觀人類生存圖景、發展壁壘、社會異像、現代化進程中個中問題進行窺視,不同的關注落腳點是對「巴別塔」隱喻的當代多義解讀,也可以是共同提出問題引導思考的嘗試。按照這個思路我嘗試去分層面解構「圍城」概念。
四個版塊:解構「圍城」
很偶然的機會,我在朋友微信分享中看到了謝炎紅的影像作品《惡之花》,她從法國作家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提取信息,並通過意象化表達構建了一個她所「看見」的虛擬而又現實的「惡之王國」。《惡之花》的原著內容觸發了我的靈感,波德萊爾對惡王國社會畸態的揭露是為了再現19世紀末巴黎人民群體的精神危機,側重於個體精神軌跡在時代浸染下的憂鬱求索。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之間的歐洲,一種強烈的憂鬱與不信任感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情緒,這種情緒之後是人們對新技術理性的反動,新世紀推動的技術進步讓人性無處安身。
無論是尼採的吶喊,王爾德的唯美追求、柏格森對非理性哲學的推崇,還是弗洛伊德對潛意識的探索。戰爭、技術、大眾文化,讓一代青年陷入絕望。於是,斯坦因指著海明威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而本雅明則把這一代青年稱為「經驗貧乏」的一代。
同樣在《圍城》方鴻漸所處的時代,在社會產生巨大轉型變革的今天,青年的困窘似乎有著驚人的相似。2017年《新周刊》公眾號推送的一篇文章《 你之所以終日惶惶,是因為一直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搖晃》,文章講述了變革時代「被中年」的青年群體集體遭遇的「中年危機」,也意欲揭露和探討這一群體沉湎於懷念過去和暢想未來蹺蹺板上不斷搖擺不確定的彷徨精神狀態。每個時代的青年都會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交織中遊離找尋,可似乎都沒有眼下年輕人如此緊張壓抑,這是時代無法迴避的困境與面相。
如果「巴別塔「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版塊呈現藝術家對宏觀城市圖景、異化現象以及現代化進程中諸多時代癥結等基於他者身份進行的懷疑反思,以此順延思考,我聯想到從另外三個層面繼續解構呈現:大時代背景包裹中的個體與自身現實處境對峙引發的精神困惑與內心衝突;作為社會獨特怪象的「成功學」價值觀給青年造成的身份選擇困惑和焦慮;青年藝術家群體對藝術空間語言的探索以及隱藏在非敘事畫面之下的混沌狀態與矛盾情緒。我最終把四個版塊依次歸納為:巴別塔、惡之花、成功學、城門開。
策展方案截圖
兩種語言,閱讀體驗的交織
當四個主題版塊的關鍵詞提取出來,我發現了有趣的點:潛意識裡的私人閱讀經驗已先主觀意識一步為我提供了靈感來源。「城門開」是對詩人北島一本書名的懸置挪用;而「惡之花」源於波德萊爾的著作;「巴別塔」的原始出處則為《聖經》。如果說「圍城」是能夠引發公共情感的一種狀態,是否可以在展場版塊聯結上以紙質書籍為由頭,通過在公共日常生活中極具親民性的文本閱讀營造代入感,當策展人私人閱讀轉變為一種對藝術文化的公共討論,當代藝術之於大眾的理解距離也具備了縮短的可能性。
文本語言、圖像語言均能給觀眾以閱讀的感官愉悅,當前者引發的想象空間與後者帶來的直接觀感彼此介入交織,在倡導回歸紙質閱讀、當代藝術貼近生活的當下,未嘗不是一種有效嘗試。但橫亘在我眼前的另一個問題是:何以避免展覽成為對藝術家來說的命題策展?以文本作品做引與藝術家創作如何生髮關聯?在策展人與藝術家之間何以建構對話機制,共同完成一場知識產出,從而打開各種意義可能性,締造學理研究對象的創造型展覽?
展覽的四條討論線
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認為,觀眾對於作品的討論和觀看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關鍵。藝術被認為應該創造一種主體溝通的場景,促成主體間話語機制的建立。盛葳老師在初步通過我的策展方案后,重點圍繞策展人、藝術家、公眾間如何藉助展覽有效對話?藝術家對展覽的積極實踐如何更立體化地得到凸顯提出了疑問,也對展覽的文獻給出了較高的要求。在他的啟發和指導下,我對展覽設置及亮點重新進行了梳理和規劃,並歸納出四條明確的學術討論線:
策展初版方案截圖
亮點歸納01「圍城」及解構出的四個版塊核心內容,作為群體狀態而更具公共接受性;藝術家的作品也因主題版塊的劃分凸顯了本體語言的智性創造和用藝術觀照時代的雙重特性。藝術家、策展人在手記互換閱讀中展開的問答討論為作品的創作與解讀、展覽的學術定位及推廣生產了理論支撐;儘管囿於主題傾向,所選作品部分為藝術家舊作,但展覽為其提供了站在當下審視過去的機會,時效性的手記寫作不僅是對過往的梳理總結,也是聯結眼下重新思考的過程,不同的時間節點回看自身的創作,有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仍在探索中,當時的理念和狀態,在今天又有何變化?亦是藉助展覽及相關線上/線下推廣得以全新呈現的。04線上線下公共互動活動的打造,為公共理解當代藝術營造了想象的空間和情感的親近;以文學作品為引串聯起的展覽觀看模式,能在公共討論區收穫更多與閱讀、藝術、文化等前沿議題有關的內容反饋。阿多諾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在商業資本過度操作與庸俗化創作如此肆意的當代,文學和藝術作為審美活動理應因其存在使人類得以在虛無的深淵中存有反抗的力量和希望,更為重要的是自身具備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必須受到承繼與發揚。藝術創作一旦脫離時代命題走向視覺空洞化、絕對自我的逼仄處境則必將淪為無意義。恢復創作主體的獨立思考與責任擔當也許正是青年一代意欲革新的新方向。我希望藉由策劃這場以解構「圍城」之態為思想主線,以公眾日常閱讀經驗為視覺線索串聯起的展覽,在人生目的消解、理想淡化、奮鬥精神衰退的當下,形成某種積極的啟示:以此告慰每位走進「閱讀」場域的觀者,擁有直面人類實際存在境況的勇氣,從理想主義與幻象破滅的消極死循環中走出,正視此在的真實與未知的永恆。而這也是我的策展初衷,亦是對展覽理想效果的美好期許。
「青年策展人項目」是2016年常青藤計劃在「青年藝術家年展」之外推出的全新項目,以項目制的方式面向國內外青年策展人徵集展覽方案,最終選擇出優秀的有效方案輔以多層面的扶持與引導,助力青年策展人將藝術構想變成展覽現實。
2017年,常青藤計劃持續推出青年策展人項目,並為入選者提供更為專項細緻的輔助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