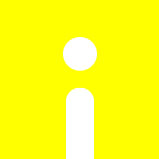▲張忠培1990年在山西省太谷縣白燕村工地庫房觀察陶鬲。
(圖片由張曉悟提供)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張忠培踩過陝西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觸摸過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遺址挖掘出的文物,走過華北、東北及內蒙古東部歷史文化區的土地。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他的足跡拼接起來,幾乎就是一塊考古遺址版圖
「先生不再是考古專家,而是考古大家」,這個「大」字,體現在張忠培濃縮了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考古大題,為考古學建構了屬於自己、具有特色的考古學理論體系,未來將引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將考古事業向前推進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完顏文豪、秦漢元
7月9日上午8點多,田建文步伐沉重地走向侯馬西站,他依然斜挎著陪伴了他多年的考古包,只不過這一次他的目的地不是遺址發掘現場。
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張星德向她所在的遼寧大學歷史學院臨時請了兩天假,匆忙趕往瀋陽北站,坐上了G400次列車。
4個小時后,高蒙河在上海西郊的家中匆匆敲完給媒體的第六篇回憶文章,合上筆記本電腦,就往虹橋車站趕去。
此後兩天里,更多的人從吉林、甘肅、陝西、雲南、廣東、河南等地的考古工地、博物館和大學課堂上抽身啟程……
11日上午8點多,他們的身影出現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外炙熱的廣場上。
9時不到,這裡的氣溫已經迅速攀升到28攝氏度。北京氣象局曾在9日發布的高溫黃色預警中預計,9日到11日本市大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將達35攝氏度以上。
熱浪中瀰漫著悲傷的情緒,田建文跟吉林大學考古專業86級的同門和早些年畢業的師兄們簡單寒暄了幾句,隨後低聲追憶起老師張忠培生前的點點滴滴。
6天前的7月5日,故宮博物院的官方網站上,一位老人的黑白肖像照片鋪滿了整個屏幕。故宮發布的訃告上寫著: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忠培先生,於2017年7月5日9時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歲。
考古大家
7月5日上午8時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高蒙河,開會前習慣性地把手機調至關機狀態。臨近中午會議才結束,一打開手機的他頓時蒙住了,屏幕上如雨點般密集彈出的消息顯示:張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
頭天晚上,高蒙河在完成張忠培先生晚年關於考古學思考的3卷書稿的編選、校訂后,在作者生平履歷中寫下(1934年——),打算把新大綱交於先生批閱做最後修改。
此前幾天里,這個吉林大學考古專業85級的碩士畢業生,還在心裡盤算著,要在一個月後的8月5日張忠培生日那天,舉辦一個小型的學術研討會,作為對先生65載學術生涯的總結。
9日下午,坐在開往北京的高鐵上,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準備在研討會上說的一段話:先生從1952年進入新第一個考古班開始,一直在求索考古學之道的實踐和方法,最終形成了「考古學之道理論」。
考古學自誕生以來已有200年的歷史,1921年從西方傳入。面對這個學術上的舶來品,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張忠培在內的幾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著,如何把國外考古學的一般技術、方法和理論與考古學的實際相結合,闖出一條具有特色的考古學道路。
最終,張忠培從考古發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這個有著3個中空袋狀足、腹部微圓的陶器,因其在獨有、器形發展鏈條完整,被考古學界稱作「歷史的活化石」。
幾十年裡,張忠培一門心思地琢磨著這個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器物,最終完成了始自於老師蘇秉琦的陶鬲研究。他在著作《陶鬲譜系研究》中,通過梳理這一器物的演變過程,讓一幅幅上古史畫卷和先民生活圖景變得鮮活可見,塵封在黃土和史書中的中華五千年歷史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高蒙河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這樣解釋先生的研究成果:「這種具有化視角的研究,意味著考古從亦步亦趨使用西方方法,發展到融合中西進而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張忠培踩過陝西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觸摸過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遺址挖掘出的文物,走過華北、東北及內蒙古東部歷史文化區的土地。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他的足跡拼接起來,幾乎就是一塊考古遺址版圖。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陽考古隊領隊許衛紅認為,老師張忠培對考古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在考古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學「三論」——「譜系論」發展了蘇秉琦的「區系類型論」,已成為考古學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國家論」豐富了蘇秉琦的「文明論」,形成了重構古今社會的新學說;「文化論」總結了文化從多元一體到統一多元的關係,提出了「傳承、吸收、融合、創新」是古今文化演進規律的新觀點。
這些理論的提出,在高蒙河看來,「先生不再是考古專家,而是考古大家」,這個「大」字,體現在張忠培濃縮了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考古大題,為考古學建構了屬於自己、具有特色的考古學理論體系,未來將引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將考古事業向前推進。
師生接力
1934年8月,張忠培出生於湖南長沙。彼時,25歲的蘇秉琦剛從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開啟了其一生的考古生涯。
童年時期的張忠培,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的燒殺搶掠,對國難家仇有著深刻的記憶。
在其生前的一次訪談中,他提起那段往事,「我的童年是從災難中過來的,長沙4次大會戰,我們就4次逃難到鄉下,最長的一次是在1944年,一家人在鄉下農村住了一年時間。」
張忠培的長子張曉悟記得,晚年時的父親喜歡看電視劇《長沙保衛戰》,看到劇中的情節總會想起童年時全家人逃難時的日子,「每次看都是淚流滿面」。
1952年,蘇秉琦在北京大學創辦考古專業,張忠培是其招收的第一屆學生。此後的幾十年裡,師生二人開始了考古事業的接力。
蘇愷之記得,父親蘇秉琦很喜歡這個「從貧寒家庭走出來、念書刻苦」的學生,總會邀請他到家裡吃飯,讓子女以他為榜樣。在兩家60多年的往來中,自然科學出身、做地震研究的蘇愷之,始終尊稱大他3歲、搞考古的張忠培為師兄。
1956年,張忠培大學畢業后,3個工作志願都填報了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要求到田野一線工作,卻被選拔留校攻讀副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參與了陝西華縣、渭南的區域性考古調查,在發掘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時,改變了過去以一個遺迹為單位的做法,把整個墓地作為一個研究單位,開創了考古學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為國內外同類考古中領先的範式。
1961年,張忠培赴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1972年創辦吉林大學考古專業並於之后組建考古學系。
帶著學生外出田野考古時,張忠培一直主張蘇秉琦「坑邊摸陶片」的教學方式,苦口婆心地囑咐學生要練就「摸陶片的功夫」,「一定要摸到陶器和陶片的精髓里、血液里,做夢都是夢的摸陶器、陶片」。
考古工地上,他跟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提醒學生要「被考古材料牽著鼻子走」,把考古材料放在第一位,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今年3月份,他在跟吉林大學考古專業1986級的研究所、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田建文的一次談話中感慨,「觀察陶器,不能只看製法,而是觀察陶質、陶色、色度、紋飾、製法、制陶技術這六個方面,當年蘇秉琦先生就是這麼觀察的,我們這一代有少數人堅持了下來,你們這一代,行嗎?」
愛徒如子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學校園裡,這個總跟墓地遺址打交道的考古專業老師,衣著簡樸,一邊抽煙一邊不緊不慢地「說著只有入室弟子聽得懂、口音很重的長沙話」,給學生傳授著自己的一套考古學理論。
站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外近百米長的弔唁隊伍中,吉林大學考古學系教授趙賓福說起這位導師時,用了「外冷內熱」「愛徒如子」八個字,「先生對學生要求非常苛刻、嚴格,特別是學術問題毫不含糊,學生見了他會發怵。」
學生時代的許衛紅,私下裡跟她的同學稱呼這個霸氣耿直的湖南老師為「張大帥」,「對他又怕又敬,每次想去見他,都要先做好接受批評的思想準備。」
多年來,每晚9點通電話,已經成了張忠培、田建文師生間雷打不動的習慣。而耐心傾聽導師的訓斥也變成了田建文日常的一種儀式。
田建文把老師的訓斥編成了300多篇的《師說》和《新師說》,發在微信朋友圈裡,作為對自己考古研究上的鞭策。今年4月3日晚9點的電話里,張忠培告誡他:「你要成為學問家,光靠手舞足蹈、貓彈鬼跳是不行的,一定要冷靜到了冰點。」還給他開玩笑說,「你知道你最大的幸福是什麼嗎?就是52(歲)了還有人每天訓你。」在另一次通話里,張忠培說「今天就不訓你了」。
寫碩士畢業論文時,趙賓福被張忠培要求做半坡文化研究。至今回憶起來,趙賓福仍覺得那麼大的題目「研究起來相當難」,「以往很多考古大家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先生又要求在此基礎上有所拔高,研究問題具有前沿性。」
張忠培鼓勵他,「要想成為一流的考古學者,就要跟一流的學者較量。」
趙賓福現在依然感激先生這種「用大題目錘鍊學生」的方式,「做這樣的研究,要下苦功夫、啃資料,一旦完成了研究,就是考古學上的標誌性成果,甚至成為每個學生一生的代表作。」
上世紀80年代,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已經成了與北大考古系齊名的院系。
課堂之外的張忠培,用「愛徒如子」來形容其實欠「精準」——蘇愷之印象中,父親蘇秉琦關愛學生比關愛子女更多,「對學生極其關愛,對子女無所謂,父親生前總說,張先生這一點最像他。」
張忠培晚年時曾對張曉悟說起過,自己對學生要求嚴格,培養出眾多優秀的考古人才,卻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有過失」。
這位田建文心中「如師如父」的老師,總給學生說「做了我的學生,我就當你終身的老師」。在吉大時,他邀請家境貧寒的學生到家裡吃飯,摸得透每個學生的脾氣。離開校園后的30年裡,他依舊注視著學生的考古研究,常打電話了解學生的近況,「有學生生病住院或離了婚,他都會擔心」。
「每次看到學生在學術上的進步和成就,張老師都會表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開心。我完成碩士畢業論文後,去北京見老師,他還帶著我們學生去密雲水庫遊玩。」1986年曾師從張忠培、現任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的張星德回憶說。
2016年5月,張忠培被診斷為肺癌。去世前的一年時間裡,除了家人和三四個學生,他不願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他總是對學生極其關愛,卻不願意看到學生為他擔心。」在追悼會現場,田建文這樣說起相識了51年的老師。
故宮「看門人」
1987年,張忠培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攝影家梁子明來到故宮,從午門、太和門到神武門,為張忠培拍了一組照片。事後張忠培把照片拿給老師蘇秉琦看,老師笑眯眯地說:「你是故宮的看門人嘛。」
然而,這位看門人「很不走運」。他在一篇文章里回憶,「上任不到兩個月,就遭遇了兩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著了,火被滅了,卻燒毀了一座明代的景陽宮。」
更讓張忠培憂心的是,他到任后才發現「故宮是個不完整的故宮」。在當時的故宮裡,除了故宮博物院外,還零零散散分佈著14個單位,「故宮的文物,除民國政府運台的以外,境內就有兩個單位占著故宮近20萬件文物。」
故宮的不完整,讓張忠培覺得,「對於一個大國來說,是很不體面的」。
在任的4年裡,張忠培為了一個「完整故宮、安全故宮、歷史故宮、學術故宮」的目標,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銳意改革,提出「保護」和「特色」是故宮博物院管理的兩大核心問題,重新確定了故宮保護範圍,編製了故宮7年發展規劃。
原來分佈在故宮裡的一些單位陸陸續續搬了出去,原本商販遍地的午門廣場得到治理,御花園得到了重點保護。這些改變之外,故宮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長王光堯認為,更重要的是張忠培為故宮設計了一套科學的管理體制,故宮的管理結束了混亂的局面,從此有了制度化和規範化的管理體系。
蘇愷之回憶說,「張先生不在意在任時取得多大的成績,他總是想著為故宮做長遠的打算」。
南京朝天宮保存庫是抗戰時期為保存1萬餘箱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而建設的。新成立后,除部分運回北京外,仍有10萬餘件文物留存在朝天宮庫房。
王光堯清晰地記得,老院長在任時一直在跟南京交涉,希望這批文物歸還故宮。
2015年10月,張忠培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深感遺憾的是,至今的故宮仍是不完整的。」
這位曾經的「故宮看門人」,直到生前幾個月里,還在四處奔走呼籲南京留存文物儘早回到故宮。
張曉悟回憶,6月27日,張忠培的學生、文物學會副會長許偉在故宮研究院作學術報告。「父親很重視,想去看看他,又不想打擾他,就在研究院大門前站了一會兒,坐車回家了。」
當天早些時間,剛從協和醫院體檢完的張忠培,讓張曉悟陪著,專程到故宮的午門前照了相。這位曾經的故宮博物院「掌門人」,似乎在向這座古老的宮殿做最後的告別。
絕筆之作
2014年,已經80歲的張忠培,回望了一生經歷過的考古學歷程,從約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中精選出代表作,以「考古學」為主題,分別以「走出自己的路」「說出自己的話」和「盡到自己的心」為名,開始著手3卷書稿的寫作和編選。
前些年裡,蘇愷之到張忠培家裡探望時,總看到這個「歲數大了眼睛不好、又不會操作電腦」的師兄,弓著背趴在桌子上塗塗寫寫。「他的書完全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家裡書桌上常備的是塗改液,寫錯了塗了再寫。」
張忠培總喜歡讓田建文給他一些批評意見,有時田建文說不出來老師的書哪兒不好,還會遭到老師的一頓訓斥。
田建文2017年3月9日記錄的《新師說6》中,張忠培言語間表露出了些許責怪,「我的『自序』就沒有不對的地方嗎?一個看不出別人錯誤和不足的人,就沒有好好看書。明天,你用鞭子狠狠地抽我(的文章),怎麼沒有人說我不好啊?」
3月12日記錄的《新師說7》中,這位老師又向學生感慨:「我們那時對蘇秉琦先生,不像你這樣對我的,我的什麼事在你看來都是好好好,這不行。蘇先生給我講了,有什麼不同意見我就說『蘇先生,你說的有道理,不過……』,教學相長,互相切磋,這樣才能進步。」
病魔並沒有打亂張忠培的著書計劃。高蒙河回憶,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裡,先生為了3本書,常要每天工作七八個小時,直至去世前一周。
「『元君廟的前前後後』這一部分,幾經修改,到今年他仍不滿意,竟然不顧身染沉痾,再度披掛上陣,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三卷著作真是張先生『嘔心瀝血』的絕筆之作。」田建文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
高蒙河評價說,「這三卷著作評析了近百年考古學史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及其發現成果和創新成果,足以體現考古學一百年來的思想精髓,堪稱一部濃縮版的《考古學思想史》。」
未了心愿
在張忠培去世前幾個月里,他過著跟此前多年一樣的生活,不停地給學生打電話,了解他們的學術進展。5月份他還去故宮給英國杜倫大學考古系的師生講了《故宮考古、保護和研究——兼談考古學的方法論》。
6月30日是蘇秉琦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9月份,蘇秉琦先生生前的《西安考古調查報告》經整理后將出版發行。在張忠培的設想中,他要為此籌辦一次新書發布會,作為對已故老師的紀念。
「我本想6月底給師兄打電話,問問要不要我準備發言,老伴說天熱先別打擾他。再過幾天他就去世了,沒來得及打電話,他有好幾個事沒做完,就撒手了。」蘇愷之努力控制著悲痛的情緒,緩一會兒說一句地講著張忠培生前未了的心愿,說完已泣不成聲。
此前一些天里,在北京小石橋衚衕11號院的故宮宿舍里,他還像往常一樣,牽著老伴馬淑芹的手在院子里遛彎,見到老人、小孩都上前打聲招呼。
59歲的物業工作人員李俊生印象中,這個「從來不端著、一點架子沒有」的老爺子,在院子里總是很熱心,「誰家趕上事兒了,總會去過問過問。鄰居家屋子剛裝修完,他囑咐著多放放(甲醛味兒),別急著住進去。」
7月初的那幾天,李俊生隱約察覺到了一些異常。院子里總有一輛小麵包車進進出出,她問了司機才知道是「老爺子把家裡一屋子的藏書全部捐給了故宮」。
張曉悟眼中,父親是個工作狂,「一年裡常常有10個月在野外考古,家裡的事從來不管、不問,每天早出晚歸,把家當成了旅店。」
張忠培喜歡看激烈的對抗場面,在大學時愛打籃球。到了晚年,這個倔強的老爺子還迷著看NBA比賽。子女們擔心他的身體,每次球賽開始前,都會為他準備好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和一杯茶。
這個多年來常為工作顧不了家的老人,總覺得老伴操持了一輩子家裡的大小事,很不容易。臨終前幾天,他一再囑咐張曉悟「要照顧好母親」,藏了一肚子想對老伴說的話,也沒力氣說了。他就把心頭的千言萬語濃縮成一句「老馬萬歲」。
張曉悟後來聽母親說,7月初的那幾天,父親晚上睡覺時一定要撫摸著母親的手,對她戀戀不捨,「他很眷戀這個家,很眷戀這個關心他、愛護他的世界。」
7月11日10時,在回蕩著李叔同《送別》曲的告別廳里,蘇愷之向這位相交了60年的師兄做了最後的告別。隨後被老伴攙扶著,從告別廳顫顫巍巍地走了出去。當走到門外一側的電子屏幕前時,這位80歲的老人突然停住。
這張循環展示著張忠培生前影像的屏幕上,恰好切換到一張蘇秉琦和張忠培一起坐在沙發上的老照片。蘇愷之盯著那張兩位已故父兄的合照,一滴眼淚從他眼角滑落。
52歲的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何流,在聽到張忠培去世的消息時,心中生出一句感慨,「真是大師的時代要過去了」。
站在弔唁隊伍中間,她說起自己總有一種奇特的感受,「跟參加別的追悼會覺得心酸想哭不一樣,這次總感覺老先生並未遠去,他身上那種老一輩考古大家的精神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