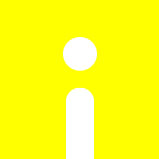新銳散文
情懷溫度
情感,思想,
角度,視野
汪曾祺談寫作
汪曾祺
我寫的東西很少,看的也不多,而且沒有理論,不善於邏輯思維,亦無經驗可言,與你們不同的一點就是歲數大一些。古人說一個人沒出息在於「以年長人」,我只剩下了「以年長人」,因而今天只是隨便漫談。
第一個問題,作家要認清自已是什麼樣的作家,具備什麼樣的氣質。
法國的一位漢學家訪何我時說:我首先問你一個你自己很難回答的問題,你覺得你在文學上的位置如何?我們先撇開這個話題扯點別的。當時我問翻譯要不要請這個法國人到家裡吃頓飯,翻譯說他很願意到人家裡吃飯。結果我親自給他做了菜。法國人口味很刁,他不會感興趣,給他吃牛排和雞就更不行了。於是我琢磨了幾個菜,非常簡單,且不影響與他談話。這幾個菜之一是煮毛豆,把毛豆與花椒、大料、鹽放在水裡一煮;再一個是炒豆芽菜;還有一個是茶葉蛋。再說主食,吃麵包不行,法國的麵包是世界最好的,米飯也不會喜歡,結果我給他炒了一盆福建米粉,又做了碗湯,他連著說:「好吃,好吃。」抓起毛豆連皮整個兒往嘴裡塞,法國人知道怎樣吃大豆,但不知道毛豆的這種吃法。我問他在法國有沒有炒豆芽菜,他還說,在飯店見過,也吃過,但我炒得更有些特點。其實我的豆芽菜很簡單,炒時擱幾粒花椒,炒完后把花椒去掉,起鍋時噴點兒醋,所以很脆,不是咕嘟咕嘟煮出來的。雞蛋全世界都有,但用茶葉煮雞蛋他沒吃過。炒米粉他也沒吃過。另外我給他做了個湯,他不吃豬肉。我說我非得讓你吃點豬肉湯是用福建的燕皮丸做的,燕皮是把豬肉搗成泥摻點澱粉扦成的,像餛飩皮,裡面包上精緻的餡,他以為是餛飩,連說好吃。所以,讓外國人能夠欣賞,得是粗東西。
這位法國漢學家說了個笑話,說世界有四大天堂四大地獄,四大天堂之一是的飯菜,之二是美國的工資、之三是日本的女人,之四是英國的住房;反過來,四大地獄之一是日本的住房,美國的女人,英國的飯食,的工資。所以,我必須給他做地道的玩藝。也有人說,文學要走向世界必須有地道的味兒,跟菜似的,我為什麼要給他做的家常菜呢?寫作也一樣,不但要有味兒,還得是家常的。家常菜也要做的很細緻,很講究。我做的那碗湯除了燕丸外還放了口蘑,但湯做的好后我把口蘑撈出去了,只留下口蘑的香味鮮味。寫作品也一樣,要寫得有味兒,且是普普通通的家常味,但製作時要很精緻講究,叫人看不出是講究出來的。我喜歡琢磨做菜,有人稱我是美食家。寫作和做菜往往能夠聯繫起來。
那位法國漢學家問:「你自己覺得你在文學中的位置是什麼?」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說了兩點:「首先我不是一個大作家,我的氣質決定了我不能成為大作家。」我覺得作家有兩類,一類寫大作品,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福樓拜,另一類如契訶夫,他的小說基本上是短篇,有個西班牙作家叫阿佐林,阿佐林也寫長篇,但他的長篇就像一篇篇的散文。所以,每個人概括生活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作家應該讀什麼樣的作品?我認為很簡單,讀與自已氣質比較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文學史家應該全面完整,評論家可以有偏愛,但不可過度。一個作家,不單有偏愛,而且必須有偏愛。我承認你的作品很偉大,但我就是不喜歡。托爾斯泰的主要作品我都讀過,倒是比較喜歡他的不太重要的作品,如《高加索的人》等。《戰爭與和平》從上大學開始,看了幾次沒看完,直到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勞動改造,想想得帶幾本經典的書,於是帶兩本《戰爭與和平》,好不容易看完了。巴爾扎克的東西了不得,百科全書,但我只是禮貌性地讀他的作品。
作家看東西可以抓起來就看,看不下去就丟一邊。這樣才可能形成你自己的風格,風格總是一些與你相近的作家對你施加影響,它不是平白無故形成的,總是受了某些作家的影響加上你自己的東西,形成獨特的風格。完全不受人影響,獨立自主地形成了一種風格,這不容易。在外國作家中,始終給我較大影響的是契訶夫,另外一個是西班牙作家阿佐夫。法國作家中給我一定影響的是波特萊爾。蘇聯作家安東諾夫、舒克申的作品,我比較喜歡。
一個作家要形成自己的風格,一方面要博覽,另一方面要有偏愛,擁有自己所喜愛的作家。明朝散文家歸有光對我影響極大,我並未讀過他的全部作品。這是個很矛盾的人,一方面有正統的儒家思想,另、方面又有很醇厚的人情味,他寫人事寫得很平淡。他的散文自成一格。他的散文《項脊軒志》、《寒花葬志》、《先妣考志》給了我很深的影響。我認為歸有光是的契訶夫。平平淡淡的敘述,平平淡淡的人事,在他筆下很有味兒。如《項脊軒志》中寫項脊軒,又叫南闔子,文中有「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闔子,且何謂闔子也?』」他沒有解釋什麼是闔子,僅記錄了這句問。《項脊軒志》的結尾很動人,但寫的極平淡,「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蓋矣。」這個結尾相當動人。所以,我傾向於作家讀那些與自己的氣質相接近的作品。「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什麼素質。
首先要對生活充滿驚奇感,充滿興趣,包括吃東西,聽方言,當然最重要的是對人的興趣。我寫過一篇雜文,題目是《口味、耳音與興趣》。有一次,遇一位中年婦女買牛肉,她問:「牛肉怎麼吃?」周圍的人都很驚奇。她說:「我們家從來不吃牛羊肉。」「那你幹嘛買牛肉?」她說:「我的孩子大了,他們要到外地去,我要讓他們習慣習慣。」這位母親用心良苦,於是我給她講了牛肉的各種做法。
一個作家如果這也不吃那也不吃,口味單調可不是好事情。還要學會聽各地的方言,作家要走南闖北,不一定要會說,但一定會聽,對各地的語言都有興趣。周立波是湖南人,但他寫的《暴風驟雨》從對話到敘述語言充滿了東北味兒。熟悉了較多的方言,容易豐富你自己的語感;熟悉了那個地方的語言,才能了解那個地方的藝術的妙處。作家對生活要充滿興趣,這種興趣得從小培養。建議你們讀讀《從文自傳》,他自稱為頑童自傳,我說他是美的教育、告訴人們怎樣從小認識美、認識生活、認識生活的美。如這一段記述:「學校在北門,我住的是西門,又進南門,再繞城大街一直走去,在南門河灘方面我還可看一陣殺牛,機會好時、恰好看到那頭老實可憐的畜牲放倒的情形,因為每天可以看一點點。殺牛的手續與牛內髒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再過去一點,是邊街,有織席子的鋪子,每天任何時間皆有幾個老人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鋼刀破篾,有兩個小孩子蹲在地上織席子,(我對這行手藝所明白的種種現在說來似乎比寫字還在行)……」這種隨處流連是一個作家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有人問:你怎麼成為作家了?我回答了四個大字:東張西望!我小時候就極愛東張西望。對生活要有驚奇感、很冷漠地看不行。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對好眼睛、一雙好耳朵、一隻好鼻子,能看到、聽到、聞到別人不大注意的東西。沈從文老師說他的心永遠要為一種新鮮的顏色、新鮮的氣味而動。
作家對色彩、聲音、氣味的感覺應該比別人更敏銳更精細些。沈老師在好幾篇小說中寫到了對黃昏的感覺:黃昏的顏色、各種聲音、黃昏時草的氣味花的氣味甚至甲蟲的氣味。簡單的說,這些感受來自於觀察、專註的觀察,從觀察中看出生活的美,生活的詩意。我小時候常常在街上看打小羅漢、做竹器等,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有戶人家的漆門上的蘭色對子「山似有骨撐千古,海經能容納百川」,不知不覺被我記住了。我寫家鄉的小說《大淖記事》家鄉人說寫的很像。有人就問我弟弟:「你大哥小時候是不是拿筆記本到處記?」他們都奇怪我對小時候的事兒記得那麼清楚。我說,第一,我沒想著要當個作家;第二,那時候的紙是粗麻毛邊紙,用毛筆寫字、怎麼記呀?為什麼能記住呢?就是因為我比較細心地、專註地觀察過這些東西,而且是很有興趣觀察。——個作家對生活現象要敏感,另外還應該培養形象記憶,不要拿筆記本記,那個形象就存在於你的大腦皮層中,形象的記憶儲存多了,要寫什麼就可隨時調動出來。當然,我說過,最重要的是對人的興趣,有的人說的話,你一輩子忘不了。最近我發了一篇《安樂居》寫到一個上海老頭,這個老頭到小鋪去喝酒,這個鋪子喝一兩,那個鋪子喝一兩。有人問他,他說:「我們喝酒的人,好像天上飛著的一隻鳥,小酒店好像地上長的一棵樹,鳥見了樹總要落一落的。」他用上海話回答,很妙,翻成普通話就沒意思了。作家不單是為了寫東西而感受生活,問題是能否在生活中發掘和感受到東西。也不要求你一天到晚都去感覺。作家猶如假寐的狗,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中,聽到一點兒聲音就突然驚醒。如果一個作家覺著生活本身沒意思,活著就別當什麼作家。對生活的濃厚興趣是作家的職業病。阿城有—段時間去做生意,我問他做的怎麼樣,他說咱干不那事,我問為什麼,他說我跟人談合同時,談著談著便觀察起他來了。我說,你行,你能當個小說家。作為一個作家,最起碼的條件就是對生活充滿興趣。
創作能否教,能否學,這是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也牽扯到文學院的辦學方針問題,多數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大學時的一個老師說過,大學不承擔培養作家的任務,作家不是大學里培養出來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一定道理。也有人說創作可以教。其實教是可以教的,問題在於怎樣教,什麼樣的人來教,如果指導創作方法搞成乾巴巴的理論性的東西,那接受不了,靠講授學會創作是不可能的。按沈從文先生的觀點說,不是講在前,寫在後。而是寫在前,講在後。你先寫出來,然後再就你的作品談些問題。沈先生曾教過我三門課,一門是《個體文習作》,一門是《創作實習》,還有一門《小說史》。前兩門課程名稱就很意思,一個是習作、一個實習。沈老師翻來覆去地講一句話,要貼著人物來寫。據我理解,小說里最重要的是人物,人物是小說里主要的和主導的東西,其它部分都是次要的或者說派生的。環境與氣氛既是作者所感受到的,也必須是作品中人物所可能感受到的,景與人要交融在一起,寫景實際也就寫人,或者說這個景是人物的心靈所放射出來的。所以,氣氛即人物,因為氣氛浸透了人物。
你所寫的景是人物所感受到的,因而景是人物的一部分。寫景包括敘述語言都受所寫人物制約。有些大學生寫農民,對話是農民味的,敘述語言則與農民不搭界,與人物便不夠和諧。有一位青年作家以第一人稱手法寫一個國小生看他的女同學長的很纖秀。這不對,孩子沒這種感覺,這個人物便假了。我有篇小說寫一個山裡的孩子到農業科學研究所當一個小羊館,他的奶哥帶他去溫室看看,當時是冬天,他看到溫室里許多作物感到很驚奇,大冬天溫室里長著黃瓜西紅柿!「黃瓜這樣綠,西紅柿這樣紅,好像上了顏色一樣。」完全是孩子的感覺,如果他說很鮮艷,那就不對了。我還寫到一個孩子經過一片草原,草原上盛開著一大片馬蘭花,開的手掌般大,有好幾里,我當時經過這片草原時感覺進入了童話世界,但寫這個孩子則不能用「他彷彿走進了童話」,因為這孩子是河北農村的,沒有多少文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童話。所以我只好放棄童話的感覺,寫他彷彿在做夢,這是孩子有可能感覺到的,這種敘述語言比較接近孩子的感覺。所以我覺得議論部分,抒情部分,屬於作者主觀感受上的東西一定要和所寫人物協調。
我年輕時候寫人物對話總希望把對話寫的美一點,抒情一點,帶有一定的哲理,覺得平平常常的日常對話沒意思。沈先生批評了我,他說:你這個不是人物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大家都說聰明話,平常人說話沒這麼說的。因而,我有一個經驗,小說對話一定要寫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很日常化,但還很有味。隨便把什麼話記下來做為小說的對話也不行。托爾斯泰說:「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談的。」此話說的非常好!如若火車站候車室等車的人都在說警句,不免讓人感到他們神經有問題。貼到人物來寫最基本的就是作家的思想感情與人物的感情要貼切要一致,要能感同身受。作家的感情不能離開人物的感情。當然,作家與人物有三種關係,一種是仰視,屬於高、大、全,英雄概念的;另一種是俯視的;還有一種是平等的。我認為作家與人物要採取平等態度。你不要有意去歌頌他,也不要有意去批判他,你只要理解他,才可能把人物寫的親切。一般來說,作家的感情應該與人物貼得很緊。也有人認為作家應該超脫開人物,這也是可以的。但就我自己來說,如果不貼著人物來寫,便覺得筆下飄了,浮了,人物不一定是自己想寫的人物了。而且,貼近人物容易有神來之筆,事先並未想到,由於你與人物共甘苦、同哀樂,構思中沒想到的一些東西自然湧現了。我寫小說的習慣是想到幾乎能夠背出來的程度再提筆。貼緊人物便會得到事先沒想到的動人的東西。我寫《大淖記事》中的小錫匠與挑夫的女兒要好,挑夫的女兒被一個地方武裝的號長霸佔,指使他的弟兄把小錫匠打死,但小錫匠沒有死透,老錫匠便用尿來救他。小錫匠牙關緊閉,挑夫的女兒就在耳邊說,十一子,你把它喝了吧。小錫匠便開了牙關。
一般說來,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就好像音樂是旋律和節奏的藝術,繪畫是色彩和線條的藝術。我覺得這種說法很奇怪,說這篇小說寫得很好,就是語言不行。語言不好,小說怎麼能寫的出彩呢?就好像說這個曲子奏的不錯,就是旋律不好,節奏不好,這是講不通的。說這幅畫很好,就是色彩不好,線條不好。離開了色彩和線條哪還有畫?離開了節奏和旋律哪有音樂呢?我對語言有一心得,語言是本質的東西,,語言不只是工具、技巧、形式。若干年前。聞一多先生寫了篇文章叫《莊子》,其中說:「莊子的文字不單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我覺得很對,文字就是目的。小說的語言不純粹外部的東西,語言和內容是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我認為,語言就是內容,這可能絕對了一些。另外。作家的語言首先決定於作家的氣質。有什麼樣的氣質就有什麼樣的語言。一個作家的語言是他風格的一部分,法國的布封早就說過「風格即人」。或者還可以說,作家的語言也就是作家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一個作家的語言是別人不能代替的。魯迅和周作人是哥倆,但語言決不一樣。有些人的作品可以不署名,一看就知道。語言的特色一方面決定於作家的氣質,另一方面決定於作家對於不同的人事的態度。魯迅寫《故鄉》、《祝福》是一種語言,寫《肥皂》、《高老夫子》又是一種語言。前一種是因為魯迅對所寫的人事的態度。語言里很重要的是它的敘述語調,你用什麼調子寫這個人、這件事,就可看出作家對此人此事此種生活的態度。語言不在詞藻,而在於調子。對人物的褒貶不在於他用了什麼樣的定語,而在於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情感傾向。作家的傾向性就表現在他的語言里。的說法是褒貶,外國的說法是傾向性。褒貶不落在詞句上,而在筆調上。的春秋筆法很好,它對人事不加褒貶,卻有傾向性。《左傳》中的《鄭伯克段於鄢》,本是哥倆打仗,他們之間本沒有什麼一定的誰是誰非。《史記》中敘述項羽與劉邦的語調截然不同。所以,我認為要探索一個作家的思想內涵,觀察它的傾向性,首先必須掌握它的敘述語調。探索作家創作的內部規律、思維方式、心理結構,不能不琢磨作家的語言。魯迅《故事新編》中的《採薇》寫叔齊吃松針面,「他愈嚼,就愈皺眉,直著脖子咽了幾咽,倒哇的一聲吐出來了,訴苦似的看著叔齊道:『苦……粗……』。這時候,叔齊真好像落在深潭裡,什麼希望也沒有了。抖抖的也拗了一角,咀嚼起來,可真也毫沒有可吃的樣子:苦……粗……」如果把「苦」、「粗」改成「苦澀」、「粗糙」,那麼魯迅的溫和的諷刺,魯迅的幽默就全沒了。所以,從眾和脫俗看似矛盾其實是一回事。
語言的獨特不在於用別人不用的詞,而在於他能在別人也用的詞中賦予別人所想不到的意蘊。詩話中有談到古詩:「白楊鄉悲風,蕭蕭愁煞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用在此處則最佳。魯迅所用的字人們也都用,但卻用不出那味兒來。如魯迅《祝福》中寫魯四老爺一見面便「是寒喧,寒喧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但是,談話總也不投機,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裡。」「剩」字很一般,但用的貼切、出眾。沈先生的文章中有:「獨自一人,坐在灌滿了涼風的船頭。」「灌」字用的很好,又比如他寫一個水手看人家打牌,說他「鑲」在那裡,太準確貼切了。語言是應該有獨創性,但不能獨創別人們不懂的地步,語言極重要的是要用字准。蘇東坡寫病鶴道:「三尺長脛擱瘦軀」,這個「擱」字一下子就顯出了生病的仙鶴。屠格涅夫的語言也相當準確,寫伐木,「大樹緩慢地莊重地……」「莊重的」用的極妙,包含很多意思在內,融注了感情,這種語言是精到的。我寫馬吃夜草,琢磨了很久才寫下「馬在安靜地、嚴肅地吃草料。」用詞不必求怪,寫出人人心中皆有、筆下卻無的句子來就好。
還要注意吸收群眾普普通通的語言,如若你留心,一天至少能搜集到三句好的語言。語言為什麼美,首先在於能聽懂,而且能記住。有一次宣傳交通安全的廣播車傳出這樣的話:橫穿馬路,不要低頭猛跑,此話相當簡煉準確,而且形象。還有一次看到一個派出所宣傳夏令衛生,只有一句話,很簡單,但很準確,「殘菜剩飯必須回鍋見開再吃。」此句中一個字也不能改動。街上修鑰匙的貼了這樣一張條;「照配鑰匙,立等可取。」簡煉到極點。語言要講藝術性,給人一種美感,同時要產生實際作用。西四牌樓附近有個鋪子邊貼了張紙條寫道:「出售新藤椅,修理舊棕床。」這就很講藝術性,平仄不很規整,但還是對仗的。我在張家口勞動時,群眾批評一個個人英雄主義的人說:「一個人再能當不了四堵牆,旗杆再高還得兩塊石頭夾住。」這話非概念化,但極有哲理。在寧夏時有位朋友去參加「花兒會」,在路上發現一對婆媳一路上的對話都是詩,都是押韻的。媳婦到娘娘廟去求子,跪下來禱告詞極棒。她說:「今年來,我跟您要子;明年來,我是手裡抱著,咯咯咯咯地笑著。」我的朋友說:「我還沒聽過世界上這麼美麗的禱告詞。」所以,群眾語言是非常豐富的,要注意從群眾語言中吸取營養。另外,還要向過去的作品學習,古文這一課還是應該補上;其次,還應該同民間文學學習,學一點民歌。不讀若干首民歌,當不好作家。學習民歌對我的寫作極有好處。這是我的由衷之言,特別是它們影響了我的語言和敘述方法。我學習的民歌主要是抒情性的,有時便想,民歌中有哲理詩嗎?後來碰上一首,是寫插秧的。「赤腳雙雙來插田,低頭看見水中天。行行插的齊齊整,退步原來是向前。」再其次,也要讀一點嚴肅文學以外的東西。如戲曲等,那裡面往往有許多對寫小說有啟發的東西。
新銳散文請支持如下稿件:人性之美、大愛情懷、鄉愁、
親情友情愛情、生態情懷、性靈自然等。
投稿郵箱:
新銳散文
長按關注